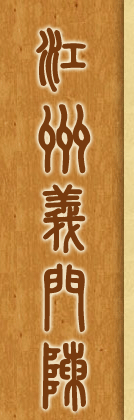- 燕叙堂的来历
- 关于西周陈国世系增加两代人的问题
- 陈叔慎战死之谜
- 关于28±4年的传代常数
- 《宋史》与《义门记》的世系比较
- 以《江南录》《义门陈氏书堂记》《通鉴续编》 佐证《宋史• 陈兢传》的正确性
- 前言
- 自序
- 《陈氏书堂记》的作者不是徐锴
- 胡旦辨
- 参加九江市义门陈研究视频会有感
- 龙峰谱中的时间矛盾再考
- 从《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推陈京生年
- 德化陈氏故里故居的演化及文德翼序
- 读《陈氏研究论文选》的一点感悟
- 义门陈世系考证的历史与现实
- 陈元光籍贯新考
- 果石庄的悲哀:部分人读不懂老谱,对错不分
- 《宋史•陈兢传》与《唐表》之辨证
- 虞舜简介
- 颍川侯陈轸文化广场
- 也论“其先盖”
- 《唐表》与《宋史》谁更可靠
- 就陈义祥《尊重史实,查找真相,寻求共识》一文之点评
- 以古人取名习惯论“异流同源”
- 《中华义门陈氏大成谱》质疑 ----致《国谱》总编陈峰先生
- 陈志高世系考兼与武亮宗亲商榷
- 再论志高是叔慎之子
- 由唐代避讳三论志高是叔慎之子
- 就《四论“叔明子志高”》同武亮再商榷
- 回复文昌宗亲文
- 驳斥陈义祥代均时间谬论
- 以他姓合族同居的代均来证义门陈是“异流同源”
- 从义门陈十五代分庄看考证后源流世系的正确性
- 关于28±4年的传代常数
- 关于大小陈旺
- 关于义门分庄的几个问题思考
- 罗韬《赠摄邑令陈都干承逸》真伪再考
- 分庄诏的由来
- 究竟是谁错了
- 老谱新论
- 柳溪陈氏与义门陈氏之世次和时间对比分析
- 论陈叔慎十八岁连生二子之合理性
- 浅谈周必大《跋德化县陈氏义门碑》
- 史书互参辨证
- 唐宋明清皇帝传世代均时间一览表
- 《义门记》新解
- 关于《由豫章罗氏姻亲新考兼旺同代》的一点补充
- 由豫章罗氏姻亲考兼旺同代
- 综合考证,正确理解义门世系
- 给“中华义门陈联谊总会”陈德友的一封公开信
- 对于《倡导“义门陈氏异流同源”之说者,是否正真秉承“以史为证、以史证谱”?》之点评
- 驳斥铭轩之谬论
- 驳义门总会不学无术,求权求名不求实----以史为据,正确辨析义门世系
- 评《江州义门》一书
- 浅谈周必大《跋德化县陈氏义门碑》
- 讨论求共识,务实是目的
- 关于考证义门陈旺世系的经过
- 《义门记》新解
- 陈檀非陈旺父、伯宣子
- 义门陈氏因讼析居
- 读《宋代国史修撰考略》而想起
- 讨论求共识,切莫忽悠人
- 这就是“唐陈伯宣活动年代考” ---从上至下梳理分析说
- 以唐代代均再论义门“异流同源”
- 陈兼生平事略新考
-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论《义门“异流同源说”质疑》
- 陈镛(镶)与伯宣
- 《义门记》新解
- 陈伯宣生卒考兼与陈义祥商榷
- 驳陈义祥《唐陈伯宣活动年代考》

读《宋代国史修撰考略》而想起
《宋代国史修撰考略》云:“宋代的文化发展颇为繁盛,在经学、史学、文学、哲学、艺术、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宋人也极为重视,这是建国之后右文基本国策实施的必然结果,也与宋儒对于历史文献本身功能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宋亡后,宋臣董文炳就曾说过:“国可灭,史不可灭。”⑴突出地体现了国史在宋儒眼中的地位,同时也证实了宋人对历史记载重要性的认同。
国史修撰作为正史编纂的一个重要前提,肇始于后汉《东观汉记》,而大成于唐代吴兢等人所撰的《唐书》,具有本纪、列传、志、表等体例,有如前代之正史,易代以后,即据此来编纂前朝正史。宋代极为重视国史的修撰。宋朝所修国史,当时亦称为“正史”,今皆散佚。据文献记载,宋朝所修国史,自太宗雍熙四年( 987) 开始命官修太祖朝正史,代代相续,迄宝祐五年( 1257) 进高、孝、光、宁四朝国史,共修成十三朝正史。计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150卷;仁宗、英宗《两朝国史》120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350卷;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国史》仅成草稿,卷数不详。宋朝国史,亡国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抵就宋国史旧本稍作编次,旋而立就。据史书记载,元顺帝(1368 ~ 1370)时,命脱脱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三史如此多的卷帙,不及三年修成,主要就是宋、辽、金各朝都有自己的国史,所以正史成书极为易事。赵翼对此就说:“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绪也。”⑵
而宋代史书的完备尤为当时所瞩目。宋代国史修撰,在中国古代发展最为详备,有《起居注》,有《日历》,有编年体的《实录》,有纪传体的《国史》等。其修史机构的设置在中国古代亦最为完善,所设有起居郎、舍人、著作郎、佐郎、国史院、实录院等,分工细而职司专。《宋史·汪藻传》载,记录书榻前议论之词,则为《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为《日历》;以此修而成之,谓之《实录》,这些都构成了宋代国史修撰的基本材料。⑶由此可见,宋代国史修撰机构的异常完善,上可以超逸汉唐、下为明清所不能及。明人徐一夔在论宋代日历、实录之制详备时,便说:‘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又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问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知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史》之所以为精确也。⑷’
宋代的日历记载涉及到了吏治、诠选、军事、狱讼、外交等有关政治的多个方面,它直接为国史修撰提供基本的史料,极为朝廷所重视,并成为政事的一部分,充分显示了宋朝对历史记载重要性的认识,这也是宋代编年体史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实录、国史正是在日历的基础上,又征集官私文字严加考订后修成的。与此同时,国修史籍所汇集的大量资料,又为私家修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今考宋人所修撰的《续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都事略》等书,皆主要依据国史,可以说国史修撰的完备,成为宋代史学发展的基础。赵翼曾说:“宋代史事较为详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实录之外又有正史,足见其记载之备也。”⑸
宋代撰修国史,除以日历、实录为基础外,还通过政府命令向地方官府、臣僚、个人征集各种文献,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初修《哲宗正史》,修撰郑久中上书曰:‘文臣太中大夫以上,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并驸马都尉,或虽官品未至而有政绩在民,遗爱可纪,忠义之节显文于时,或有不求闻达终于下位,及隐逸邱园并孝悌之士,曾经朝廷奖遇,凡在先朝葬卒者,并宗室大将军及赠公侯例合立传者,要见逐人行状、墓志、神道碑、生平事迹;或有著述文字达于时务者,照证修纂。或烈女、节妇及艺术著闻者,事迹灼然,亦合书载。及中外臣僚并宗室或因哲宗赐对,亲闻圣语,或有司奏事,特出宸断,或有论议章疏事关政体可书简册者,并许编录,实封于所在官司投纳,申缴赴院。或亡殁臣僚,有本家子孙追录所闻,或收藏得旧稿者,亦并许编录,以上项投纳,仍不得增饰事节。下进奏院遍牒天下州、军、监,明行晓示,及多方求访,如无子孙,亦许亲属及门生故吏编录,于所属投纳。仍乞下吏部左右选,入内内待省、阁门、大宗正司出榜晓示,令依上件修写,直纳赴院。今来修国史合有取会事,并从本院押贴子会问。其诸处供报隐©,当行人吏,并从严断勒停,事理重者,刺配五百里外本城,不再赦原降减。急限一日,慢限三日,差错违限,从本院直牒大理寺,主行人吏,并科杖八十,罪情理重者自从重。’
南宋嘉泰三年(1203)将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傅伯寿上言称:‘中兴以来,修《徽宗实录》则采《元符诏旨》,修《四朝国史》则采《续资治通鉴》及《东都事略》。今孝宗、光宗《实录》已成,将修《三朝正史》,自建炎丁未至于绍熙甲寅六十八年,典册所书固已灿然,其间岂无登载©脱、传闻异同之患?凡事有旧记述,可不广取而参考乎? 今史馆所收《三朝北盟会编》、《中兴遗史》、《中兴小历》三书,恐如此之类尚多有之,臣以为宜发明诏,广加访求⑹。’
由上二人奏疏可见,国史修撰,除了运用日历、实录为依据外,还进行文献资料的广泛征集,从闻人达士的行状、墓志、神道碑、著述文字到烈女、节妇、隐士、孝悌的事迹;从诏文、奏议、旧稿到圣语、宸断、议论章疏等等,史馆欲通过此种方式最大限度地调集丰富的史料,以补充朝廷典册所出现的©脱,使国史能够内容充实、准确。然而,由于宋代国史的修撰多据所征集来的家传、表志、行状以及奇闻逸事等,所以出现溢美隐恶的情况,致使影响在此基础上所撰正史《宋史》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如章、吕惠卿、蔡确、蔡京、秦桧等,故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著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著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无怪乎是非失当也。⑺’
《宋史》共 496 卷,而人物《列传》就有 255卷,占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人物传记当为朝廷修国史时取自各家行状、表志、碑铭、言行录、遗事等,这些多为子弟门生所撰,自然会“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隐恶扬善,曲意书之,这样无形中就会使历史的真实性降低,可信度不高。正是由于宋朝国史如此撰述,在元代修撰《宋史》时,“悉仍其旧”,又“不暇参互考证”,所以造成了《宋史》的繁冗失当之处颇多,赵翼曾对此多有举例说明,……
参阅文献
⑴ (元)脱脱等:《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
⑵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辽金三史》。
⑶《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
⑷《明史·文苑传》及朱彝尊《曝书亭集·徐一夔传》。
⑸(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史事最详》。
⑹《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三〇。
⑺《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六十。
读后语
本文节选自《宋代国史修撰考略》,作者姜海军,1977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2004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经学、儒学等。2006年,论文发表在《文献天地》,对《宋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总结,堪称经典之作!全文见链接http://www.jzyimenchen.com/pic/jianghaijun.pdf (请复制链接用浏览器打开)
国史修撰是中国古代正史修撰的一个重要前提,宋代国史修撰在古代发展最为完备,为后代修撰前朝正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宋朝国史,亡国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抵就宋国史旧本稍作编次,旋而立就。”同时指出:“《宋史》共 496 卷,而人物《列传》就有 255卷,占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人物传记当为朝廷修国史时取自各家行状、表志、碑铭、言行录、遗事等。并由此而想起家长陈泰在天圣年间上报的《回义门累朝事迹状》说:“为修真宗皇帝一朝正史,要见义门陈氏自来义居事迹及朝廷有何恩赐、旌表,次第立便取来,仔细具录”,于是乎,《宋史·孝义列传》收录了《陈兢》文。
陈兢,义门家长,宋太宗朝人;按史谱载,为叔明第十四代孙。作为一国正史,《宋史·陈兢传》竟有如此详细的家族世系,实属难得。其史料当然来自义门家长向朝廷呈报的家传、家乘等私家材料。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宋史十六·孝义传陈兢》评述:“陈宜都王叔明之后。叔明五世孙兼,唐右补阙。兼生京,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无子,以从子褒为嗣,褒至盐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生(孙)伯宣。伯宣,即兢之高祖也。叙陈氏义门,当自伯宣始,今自灌以上一一胪列,似家乘非国史矣。”
正因为有“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无怪乎是非失当也”。因此,《陈兢传》在叙事方面存在着“溢美隐恶”的成分。
一、“百犬同槽”故事,它属于文学范畴,非史实。清人王夫之读此毫不客气地指出:“有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不食。其诞至此,而兢敢居之为美,人且传之为异,史且载之为真,率天下以伪,君子之所恶夫乱德之言者,非此言哉?人而至于百,则合食之顷,一有不至,非按而数之,且不及察矣。犬而至百,坌涌而前,一犬不至,即智如神禹,未有能一览而知者,奚况犬乎?”
二、“灌孙伯宣,避难泉州,与马总善”,此句有两处隐讳:
一是“灌子名为何不著”?事情原本是这样的:褒生灌,灌生镛、鍠,唐贞元(785-805)间,灌任高安县丞,得罪了当地豪猾,在任四年,与夫人黄氏同时被害于官舍,后灌子镛杀了仇人全家,外逃泉州仙游避难,改名镶。为隐讳,故传中略而不书其事。徐锴《陈氏书堂记》载“避难于泉州之仙游,生伯宣”,不是“伯宣,避难泉州”!正是因为隐去陈镛杀人命案,故不提“灌子名”。
二是“伯宣与马总善”,其实,与马总友善的是陈镶,而不是伯宣。《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载马总“贞元十六年(800),盈珍谗其幕僚马总,贬泉州别驾,……元和初,自泉州迁虔州刺史”。元和十四年,陈镶仍在仙游,此时伯宣尚未出世。晚年陈镶,携伯宣游®山,隐居圣治峰。
三、《宋史·陈兢传》交待义门世系,主要是宜都王叔明五世孙陈兼这一支,即从叔明起→五世孙兼→京→褒→灌→(灌孙伯宣)→崇→衮→昉→兢→延赏,到了陈延赏这一代义门开始析庄。在旧时重视门阀时代,义门人是以叔明这一支为代表呈报官府,转呈国史院;也只有这一支人当官的多,拿得出,唱得响,所以《宋史》出现了这一支人的传承情况。义门人,本是异流同源,合族同处。对于其他支系,《宋史》虽未交待,但在兢后是以“从”字巧妙地点出另一支系的几任家长,如“兢从父弟旭每岁止受贷粟之半,云‘省啬而食可以接秋成。’”“旭卒,弟蕴主家事……蕴卒,弟泰主之”云云。《宋史·陈兢传》对“从”字的运用超出本意,同一支系人,即使出了五服也一概称“弟”;只有对不同支系的同辈人,才互称“从弟”。
“正是由于宋朝国史如此撰述,在元代修撰《宋史》时,‘悉仍其旧’,又‘不暇参互考证’,所以造成了《宋史》的繁冗失当之处颇多”。尽管《陈兢传》有如此瑕疵,但由于“悉仍其旧”,故陈兢的世系才真实地流传下来。今当辩证地看待《宋史· 陈兢传》,取其精华,剔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