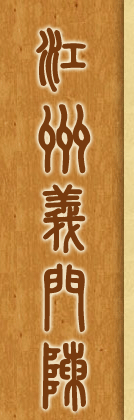- 陈氏谱考辑要目录
- 宋乾道二年族谱原序
- 都氏源流考
- 庐陵衡塘陈氏族谱序
- 义门谱中记事存疑
- 陈氏入蜀记
- 陈氏谱考辑要总论
- 陈氏谱考辑要前言
- 陈氏谱考辑要序
- 《义门陈文史考》目录
- 第一章 陈姓源流考(新考)
- 《颍川陈氏考略》目录
- 义门陈文史考第二版编委
- 义门陈文史考第二版封面
- 唐代江州的陈氏家族
- 史书互参辨证
- 陈叔荣墓志铭
- 平城县正陈子干诔并序
- 前陈沅陵王故陈府君(叔兴)之墓志
- 陈临贺王国⑴太妃(施氏)墓志铭
- 隋故礼部侍郎通议大夫陈府君(叔明)之墓志铭
- 陈寔子孙考
- 读书偶得
- 读者陈江波来信
- 读者陈军来信
- 义门陈文史续考
- 义门陈文史考
- 《义门陈文史续考》跋语
- 义门陈文史续考后记
- 义门陈文史续考前言
- 义门陈文史续考序
- 义门陈文史续考目录
- 后记
- 避兵记
- 李成匪毁义门故居
- 九里殿
- 德安义门陈村考察记
- 附二:凡例与译文
- 回义门累朝事迹状(节)
- 义门家范十二则
- 义门陈氏世系考
- 家祭与官祭
- 从九江联宗谱序看义门世系世次的演绎
- 用时间推考义门世次
- 陈伯宣迁庐年考
- 义门世次歧异成因探析
- 义 门 考 异
- 江州义门宗谱考
- 史志文摘
- 义门纪事
- 研究与考辨
- 序二
- 序一
- 义门陈文史考书讯

史书互参辨证
类别:文史 选载
涉及义门纪事和义门陈氏世系的史书,按时间先后有《陈氏书堂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新唐书·陈京传》、《资治通鉴·续编》、《南唐录》和《江表志》、《南唐拾遗记》、《宋史·孝义传·陈兢》、《通鉴续编》等一系列史籍。为了正确理解义门内部支系结构,我们把上述史书有关内容集中在同一篇文章内,通过比对互参,取其长而辨其误,故名“史书互参辨正”。
一、首先看徐锴《陈氏书堂记》(《钦定全唐文·卷八八八》)载:“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书楼。其先盖陈宜都王叔明之后曰兼,为秘书少监。生京,给事中。以从子褒为嗣,至盐官令。生瓘,至高安县丞。其孙避难于泉州之仙游,生伯宣。注《史记》,今行于世。昔马总尝左迁泉州,与之友善。总移南康,伯宣因来居庐山,遂占籍于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崇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
《书堂记》叙述义门事件与人物世次,行文虽简洁,但比较含糊,粗线条的描述。所谓简洁,就是把伯宣由闽入赣直至人口发展至千人的这样一个跨百余年的历史,仅作一句概括,含糊的是“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一句,在没有交代陈崇身世之前,紧承接伯宣而来,但又不明说他俩的关系,留给后人诸多揣测。存在问题有:
1、按多数义门谱是“瓘生镶,镶生伯宣”,《宋史》载为“瓘孙伯宣”,而「书堂记」则为“瓘孙生伯宣”,多出一个“生”字即多出一代。同时两书都错用了一个“瓘”字,本为“灌” 。
2、“昔马总尝左迁泉州,与之友善”:经查,此说与马总传记不符。据《唐书•马总传》、《资治通鉴·唐纪》、《唐刺史考》载马总于唐贞元十六年(800)贬泉州别驾,即文中所说的“左迁泉州”,元和初(806)升迁虔州刺史(今赣州南康市);此时伯宣还没有出世,何以“与之友善”?“与之友善”的应该是其父陈镶(即龙峰谱中的陈镛)避仇难泉州结识了马总,这里是把父辈的事移到子辈来写,属于记忆上的误差。
3、“崇之子蜕”:按义门谱,蜕是佗之子,伉公后。崇子是衮,官江州司户。
「书堂记」交代的世系世次,仅伯宣这一支系,上自叔明,下至伯宣、陈崇、陈恭等,交待的还比较清楚。至于陈旺支系人,丝毫未涉及。因徐锴撰文时,自己并没有到义门“览世谱,询事实”,仅凭门生前进士章谷的口述,“笔而见告,思之为碣”。章谷曾经肄业于陈氏书堂,对于陈家的事有所耳闻,但不见得十分了解。再从“前进士”之“前”字看,此时距离他在陈氏书堂读书确有一段时日了,即使了解,也不见得记得那么清楚,所以误记难免。
二、新唐书世系表是以表格形式竖着排列,即叔明→某,会稽郡司马→某,晋陵郡司功参军→兼,右补阙、翰林学士→京,以从子褒为嗣→褒,盐官令→灌,高安丞→伯宣→旺→机。
从上可以看出兼为叔明四世孙,这是「唐表」据柳宗元《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而来,中间漏缺陈京之高祖一代,由于新表不察,以‘孙’为‘子’而误。再如“灌子伯宣,伯宣子旺”这样的世次,其它史书俱无。一般史书在叙说人物世次时,都是以事件的发展引出人物,而唐表则以表格式填写,极容易填错格。象这样的错误,唐表是举不胜举,正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前言所云:“至于传刻中出现的字误、行误更是常见之事。”
同是写陈京家的事,而《新唐书·卷二百·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儒学下》却载:“京无子,以从子褒嗣。褒孙伯宣,辞著作佐郎不拜。”这里“褒孙伯宣”中间不记灌这一代,也可以理解为“孙”或“裔孙”。同时,撰修者相当谨慎,不轻易将旺、机父子俩系在伯宣名下。由此可见,「表」和「传」同据一书,却持不同态度。
《新唐书》成书于北宋仁宗年间,在此之前有渤海胡旦曾谪迁岭表,已亥(999)岁会赦东归。辛丑(1001)春,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法,询事实,俱知其状而写下传世之本《义门记》,可惜这篇文章没有被收进国史书籍,流传于民间,至今出现多种版本,面目俱非,难以为凭。但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义门记》的话,恐怕史书上连“旺、机”的影子都见不到,因而也就不存在“同源异流”一说了。
三、《资治通鉴续编》、《南唐拾遗记》、《南唐录》和《江表志》等文献是叙事多,记人物世次少。陆游《南唐拾遗记》仅载“陈褒,江州德安县人,唐元和中(806—820)给事中京之后,十世同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仅载:“淳化元年五月癸丑,江州言德安县民陈兢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余口,常苦食不足。”而《南唐录》和《江表志》则仅载陈崇“存殁十一代”。
上三书关于义门世系世次的起止点各有不同:“十世同居”,是以叔明六世孙陈京为一世祖,到陈延赏为“十世同居”,即京→褒→灌→镶(镛)→伯宣→崇→衮→昉→兢→延赏。而“陈兢十四世同居”则以叔明为起始祖,到陈兢为十四世,即叔明→五世孙陈兼→京→褒→灌→镶(镛)→伯宣→崇→衮→昉→兢为十四世。而徐铉《南唐录》及郑文宝《江表志》的“我家袭秘监之累功、承著作之贻训……上下和睦,存殁十一代,曾玄二百人。”也是自叔明到陈崇止,“存殁十一代”。
四、《宋史·陈兢传》记述义门人物世次与事件,比较详细,是我们研究义门历史的主要依据之一。
《宋史·陈兢传》开篇即云:“陈兢,江州德安人,陈宜都王叔明之后”,首先点明义门世系世次自叔明起,接着“叔明五世孙兼,唐右补阙。兼生京,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无子,以从子褒为嗣,褒至盐官令。褒生瓘,高安丞。瓘孙伯宣,避难泉州……后游庐山,因居德安。尝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顺初卒。伯宣子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僖宗时尝诏旌其门,南唐又为立义门,免其徭役。崇子衮,江州司户。衮子昉,试奉礼郎。昉家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昉弟之子鸿……兢即鸿之弟……”行文流畅,叙事简洁,把陈兼这一支世系世次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即叔明→五世孙兼→京→褒→瓘(灌)→镶(或镛)→伯宣→崇→衮→昉→兢→延赏,表述得一清二楚。从一世祖叔明到陈崇为十一世,到陈昉为十三世,到陈兢为十四世。
不仅如此,《宋史》还用了三个“从”字,极为精妙地把义门内部从属不同支系的人予以区分和勾画,同时还把他们的辈份作了兑换式的交待。
如“兢死,其从父弟旭”,这个“从”字表明兢、旭从属两个支系,为同辈人。“ 旭卒,弟蕴主家事……蕴卒,弟泰主之。泰弟度……从子延赏、可,并举进士。”这里“从子延赏”的“从”字,是接着陈度来的,则表明延赏、延可不属于陈度这一支派,同时交代了延赏比陈度晚一辈,为叔明十五世孙。到了延赏这一代,义门开始分家了。
“从子”一词,按《朱子语类》卷八五:“据礼,兄弟之子当称从子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称从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称族子。”然而这里的“从子”,其用意却与此不同。按陈氏义门家谱载“鸿和兢”共祖父,理应称“从弟”,而这里称“弟”,表明是同一支系人。再如“旭与蕴,蕴与泰,泰与度”几人,本属不同房下的人,是共六世祖青公,理应相互称“族弟”,但是,正因为同属陈旺这一支后裔,所以皆称弟。“京以从子褒为嗣”,是按正常礼数称呼。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编修辽、金、宋三史,由丞相托克托等奉敕撰辑(注:托克托,原作脱脱),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修成《宋史》,速度快得惊人。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史多国史原本: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而已(见《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因此《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凡《宋史》没有收录的典籍,可惜后来几乎佚失。所以,1977年中华书局《宋史》出版说明中亦如是说:“《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写到这里,编者不禁联想到义门族谱上的记载:“为修真宗皇帝一朝正史,要见义门陈氏自来义居事迹及朝廷有何恩赐旌表次第,立便取来,仔细具录”。(详见《义门陈文史考·累朝事迹状》)这即是说,在北宋国史馆里存有当年义门呈报的资料,否则《宋史》不会如此详尽。说它直接来于宋代「实录」并不虚妄。当然,其中也有“瑕疵”,即“瓘孙伯宣,避难泉州,与马总善”这一句与史不符,想必是参考了《陈氏书堂记》。
五、由于编辑《宋史》前详后略,以及南宋抗元英勇事迹多未载入,故在《宋史》成书五年之后,著名史学家陈桱《通鉴续编》便已告成问世,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和赞誉,时人谓其父子俩“史学名家”。通鉴里收录了义门一条重要史料,由于篇幅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淳化元年(990)春正月①,诏贷江州义门陈兢粟。初,陈宜都王叔明五世孙唐右补缺兼②,生秘书少监京,京生盐官令褒,褒生高安丞灌③,灌孙伯宣,避地④江州之德安,尝以著作佐郎召⑤不起,伯宣生江州长史崇,自兼至崇未尝分异⑥。崇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⑦,建书堂教诲之。唐僖宗诏旌其门,南唐又为之立义门,免其徭役。崇子江州司户衮,衮子奉礼郎昉⑧,昉之世同居,长幼凡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⑨,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乡里率化,争讼稀少。唐亡,州上其事,诏仍旧免其徭役。昉弟子鸿,鸿弟兢。兢之世子姓益众,常苦乏食。至是知州康戬言于帝,诏本州每岁贷粟二千石。其后兢死,从弟旭止受贷粟之半,云省啬而食可以及秋成。属岁歉粟贵,或劝旭全受而粜之,可邀善价。旭曰:“朝廷以旭家群从千口,轸⑩其乏食,贷以公粟,岂可见利忘义耶。”帝闻,深加叹奖。旭后世守家法,久而不坠。(见《四库全书·通鍳续编·卷四》)
注释:
① 春正月:一般文献中只说“淳化元年”贷粟,这里准确到“春正月”,正是来自北宋国史实录。
② 缺:“阙”与“缺”,古通用。
③ 灌:此处纠正了《陈氏书堂记》等书之“瓘”。
④ 避地江州之德安:“避地”,用得极为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唐乾符四年(877),黄巢兵帅柳彦璋攻陷江州,大肆剽掠,为避兵乱,伯宣举家迁德安同旺公后人合族同处,时伉公为家长。那时的德化、德安两地虽同属江州浔阳县管辖,但是德化白鹤乡株岭距离江州城很近,且又正当驿道;而地处德安西部偏远山区的常乐里却很安全,因而伯宣“避地江州之德安”。
⑤ 召:此“召”恰当,非义门族谱中所用的“诏”。如果真是“诏征不起”的话,岂不抗旨不遵?要知道在封建社会,抗旨不遵是重罪。
⑥ 自兼至崇未尝分异:这一说法极为妥当。关于义门世系世次,一般文献都以宜都王叔明为一世祖往下数,数到陈延赏为十五代,义门开始分家,于是遂言“同居十五代”。如此说法既不符事实,也不科学。则无论是“十世同居”还是“陈兢十四世同居”,以及“昉家十三世同居”,其侧重点是好计世次脉络,而皆疏忽了“同居起始”时间这个问题,失之严谨。
按义门谱及有关资料,兼,开元十二年中进士,初官江州,后迁任封丘县丞,及后辞官归田泗上,至晚年才补阙翰林院学士,详见本书《陈兼生平事略》。陈旺,开元十九年建庄德安常乐里永清村(今义门村),按理说此句应该写成“自旺至崇未尝分异”,但是陈崇是兼公后裔,不能这么写,反正兼、旺同时同代同宗同祖,不是从兄弟也是族兄弟,作如此叙说,从计算同居起始时间及同居代数这个层面上来讲,是不误事的。
⑦ 择群从掌其事:整句意思是说大家一致推举陈崇任义门第三任家长,即《义门记》中所说的“青,显祖也。伉,二世长也。崇,三世长也”。“择群从”:是不违拗大家的意愿。“掌其事”:即任家长和管理家族事务。
⑧ 奉礼郎:古代官衔制,是官名。原本“治礼郎”,高宗即位,为了避高宗李治的讳,故改名为“奉礼郎”。此官品级因朝代不同而不同,从九品、从八品、从六品的都有。
⑨ 姻睦: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关于“姻睦”一辞,出现在旧谱陈崇家法序言里,一般不注意“姻睦”的用意,后人差不多都改成“和睦”了。近日查德安聂桥镇永丰村栗坑罗氏族谱《源流篇》得知:其“三十三世天相,赘江州义门陈吴国公兰女,因家长(常)乐里。”谱未载天相之生年,然载其父“仪闻,生唐至德丙申(756)年”,另在其《乾隆三年南关罗氏宗谱原序》中亦载:“以企生一十七世孙天相娶江州义门陈兰女,遂自吉水溪下徙历陵长(常)乐里居焉。厥后瓜瓞繁衍,乃有分居,犹自相往来,有欲相聚之意。”“有欲相聚之意”,是说在义门这一拨罗氏人,想归宗。历陵,唐朝前德安旧名。
这一记载可信,因在唐时旺公位下接连几代单传,人丁不旺,至青公始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庭兴旺起来。到大顺初陈崇制订家法时,正是“十七而三十四”之阶段,想必此时罗氏族裔在义门也有一定的人数,所以在用词上不得不考虑到这一拨人的感受,或许还有其它姻亲在内。故用“姻睦”而不用“和睦”,《宋史》亦同。
⑩ 轸:这里有轸恤,顾念和怜悯的意思。
按语:
《通鉴续编》与《宋史》就其内容大同小异,然而《通鉴续编》却补《宋史》的不足和修正宋史的瑕疵。即《宋史》说“伯宣与马总善”,《通鉴续编》无此一说,予以否定。《宋史》说“昉家十三世同居”,《通鉴续编》纠正为“自兼至崇未尝分异”,这一纠正准确地反映了义门同居起始时间及代数。另外还纠正了一个错用字,即试奉礼郎”的“试”。 不是“试奉礼郎”,原称是“太常寺奉礼郎”,故删去了“试”。
《通鉴续编》语言精练,叙事准确,几乎通篇挑不出毛病,尤其在世次之间过渡,不产生丝毫岐义,它与《宋史》合起来反映义门事件、人物世次,就清晰完备了。当然这仅是交代陈兼这一支系,至于义门内部其它支系仍未交代。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交代,因为当年义门陈对外宣传的也就是以这一支人为义门代表,连旺公裔孙陈泰的《义门累朝事迹状》亦如此,还能怎么说?在义门,也只有这一支人为官的多,上自宜都王,中有“父子两秘监”,下有伯宣、陈崇、陈衮、延赏等,对外能够唱得响,尤其在那门阀森严的等级社会里,象陈旺这样的布衣草民是难以登大雅之堂,这是其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陈朝王室众弟兄中惟叔明贤孝,形象最好。如上个世纪90年代洛阳邙山上一墓地出土的康氏《大唐故正议大夫易州遂城县令上柱国康公墓志铭并序》亦载:“陈叔明之哭父,吐 血崩心;王叔治之丧亲,邻人罢社。”曾在隋唐时期,世人一直把这二人奉为忠孝道德楷模来景仰,故南陈子孙多崇叔明为祖。
① 春正月:一般文献中只说“淳化元年”贷粟,这里准确到“春正月”,正是来自北宋国史实录。
② 缺:“阙”与“缺”,古通用。
③ 灌:此处纠正了《陈氏书堂记》等书之“瓘”。
④ 避地江州之德安:“避地”,用得极为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唐乾符四年(877),黄巢兵帅柳彦璋攻陷江州,大肆剽掠,为避兵乱,伯宣举家迁德安同旺公后人合族同处,时伉公为家长。那时的德化、德安两地虽同属江州浔阳县管辖,但是德化白鹤乡株岭距离江州城很近,且又正当驿道;而地处德安西部偏远山区的常乐里却很安全,因而伯宣“避地江州之德安”。
⑤ 召:此“召”恰当,非义门族谱中所用的“诏”。如果真是“诏征不起”的话,岂不抗旨不遵?要知道在封建社会,抗旨不遵是重罪。
⑥ 自兼至崇未尝分异:这一说法极为妥当。关于义门世系世次,一般文献都以宜都王叔明为一世祖往下数,数到陈延赏为十五代,义门开始分家,于是遂言“同居十五代”。如此说法既不符事实,也不科学。则无论是“十世同居”还是“陈兢十四世同居”,以及“昉家十三世同居”,其侧重点是好计世次脉络,而皆疏忽了“同居起始”时间这个问题,失之严谨。
按义门谱及有关资料,兼,开元十二年中进士,初官江州,后迁任封丘县丞,及后辞官归田泗上,至晚年才补阙翰林院学士,详见本书《陈兼生平事略》。陈旺,开元十九年建庄德安常乐里永清村(今义门村),按理说此句应该写成“自旺至崇未尝分异”,但是陈崇是兼公后裔,不能这么写,反正兼、旺同时同代同宗同祖,不是从兄弟也是族兄弟,作如此叙说,从计算同居起始时间及同居代数这个层面上来讲,是不误事的。
⑦ 择群从掌其事:整句意思是说大家一致推举陈崇任义门第三任家长,即《义门记》中所说的“青,显祖也。伉,二世长也。崇,三世长也”。“择群从”:是不违拗大家的意愿。“掌其事”:即任家长和管理家族事务。
⑧ 奉礼郎:古代官衔制,是官名。原本“治礼郎”,高宗即位,为了避高宗李治的讳,故改名为“奉礼郎”。此官品级因朝代不同而不同,从九品、从八品、从六品的都有。
⑨ 姻睦: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关于“姻睦”一辞,出现在旧谱陈崇家法序言里,一般不注意“姻睦”的用意,后人差不多都改成“和睦”了。近日查德安聂桥镇永丰村栗坑罗氏族谱《源流篇》得知:其“三十三世天相,赘江州义门陈吴国公兰女,因家长(常)乐里。”谱未载天相之生年,然载其父“仪闻,生唐至德丙申(756)年”,另在其《乾隆三年南关罗氏宗谱原序》中亦载:“以企生一十七世孙天相娶江州义门陈兰女,遂自吉水溪下徙历陵长(常)乐里居焉。厥后瓜瓞繁衍,乃有分居,犹自相往来,有欲相聚之意。”“有欲相聚之意”,是说在义门这一拨罗氏人,想归宗。历陵,唐朝前德安旧名。
这一记载可信,因在唐时旺公位下接连几代单传,人丁不旺,至青公始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庭兴旺起来。到大顺初陈崇制订家法时,正是“十七而三十四”之阶段,想必此时罗氏族裔在义门也有一定的人数,所以在用词上不得不考虑到这一拨人的感受,或许还有其它姻亲在内。故用“姻睦”而不用“和睦”,《宋史》亦同。
⑩ 轸:这里有轸恤,顾念和怜悯的意思。
按语:
《通鉴续编》与《宋史》就其内容大同小异,然而《通鉴续编》却补《宋史》的不足和修正宋史的瑕疵。即《宋史》说“伯宣与马总善”,《通鉴续编》无此一说,予以否定。《宋史》说“昉家十三世同居”,《通鉴续编》纠正为“自兼至崇未尝分异”,这一纠正准确地反映了义门同居起始时间及代数。另外还纠正了一个错用字,即试奉礼郎”的“试”。 不是“试奉礼郎”,原称是“太常寺奉礼郎”,故删去了“试”。
《通鉴续编》语言精练,叙事准确,几乎通篇挑不出毛病,尤其在世次之间过渡,不产生丝毫岐义,它与《宋史》合起来反映义门事件、人物世次,就清晰完备了。当然这仅是交代陈兼这一支系,至于义门内部其它支系仍未交代。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交代,因为当年义门陈对外宣传的也就是以这一支人为义门代表,连旺公裔孙陈泰的《义门累朝事迹状》亦如此,还能怎么说?在义门,也只有这一支人为官的多,上自宜都王,中有“父子两秘监”,下有伯宣、陈崇、陈衮、延赏等,对外能够唱得响,尤其在那门阀森严的等级社会里,象陈旺这样的布衣草民是难以登大雅之堂,这是其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陈朝王室众弟兄中惟叔明贤孝,形象最好。如上个世纪90年代洛阳邙山上一墓地出土的康氏《大唐故正议大夫易州遂城县令上柱国康公墓志铭并序》亦载:“陈叔明之哭父,吐 血崩心;王叔治之丧亲,邻人罢社。”曾在隋唐时期,世人一直把这二人奉为忠孝道德楷模来景仰,故南陈子孙多崇叔明为祖。

陈桱,字子经,元末明初浙江奉化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史学之家。陈桱祖父陈著(1214~1297) ,宝祐四年(1256)和文天祥同榜进士,曾任光州教授、鹭洲书院山长、太学博士等职,官至台州知府,有《本堂集》传世。陈桱父亲陈泌,历任校官、西湖书院山长,官至饶州教授。叔祖陈观、伯父陈深、陈瀹、陈洵,皆诗章翰墨足可称世,在当时是有一定知名度。在这样一个家学根基比较深厚的环境里,陈桱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史学熏陶,故“学问早成,流辈莫敢与并者”,从而成为一代著名的史学家。
陈桱有史著多种,现可考知者有:《通鉴续编》二十四卷、《续编宋史辨》一卷、《通鉴前编举要新书》二卷(已佚) 、《治平类要》(与戴良合著,卷数不详,已佚) 、《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外记》一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