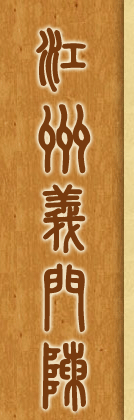- 一部客观、可靠的陈姓源流世系丨《陈氏谱考辑要》
- 陈升之与陈旭考
- 陈元光籍贯考
- 陈京及第年辨
- 陈京生平事略
- 叔达子德即清德即清考
- 陈恕籍贯与世系新考
- 伯万与陈翔辨析
- “三尧”先祖与籍贯新考
- 小公主陈婤
- 宣华夫人
- 破镜重圆——乐昌公主与徐德言
- 叔慎与叔文
- 陈寔子孙考
- 陈翔陈寔“父子”关系辨
- 陈轸生平事迹简述
- 颍川陈氏始祖陈轸再考

陈翔陈寔“父子”关系辨
东汉御史中丞陈翔与东汉颍川太丘长陈寔为父子关系,这是部分颍川陈氏族谱的说法。根据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推断,翔不但不是寔父,而且翔的年龄很可能要比陈寔小。
一是在《后汉书》中翔与寔的列传没有说翔与寔是父子关系。在《后汉书》及一般史书中,凡是父子为官者,其父子事迹均编辑于同一篇文中载传。而《后汉书·陈翔传》里不言其子“寔”,而言其“祖父珍,司隶校尉”;在《后汉书·陈寔传》里未言其父“翔”,而言及其子元方和季方。可见翔与寔不是父子关系。若陈寔真为陈翔之子,则两传中总有一传会说的。再则《后汉书·陈寔传》中出现陈寔“出身卑微”、“家贫”语类,既已跟《后汉书·陈翔传》所载相矛盾了。
二是从陈翔、陈寔受党锢之祸遭株连这一事件看,能够了解翔与寔年龄相差不大,很可能翔比寔的年龄小,因此翔与寔不可能成为父子关系。
东汉党锢之祸共有三次,从《后汉书》翔和寔的传记中看不出他们是受哪一次党锢之祸遭株连,可《资治通鉴》卷五十五却明白告诉我们:“延熹九年(166)……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太仆颍川杜密、御史中丞陈翔、陈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由此得知陈翔、陈寔是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入狱的。《陈翔传》未载翔的生年,而《后汉书·陈寔传》却载寔“中平四年(187),年八十四,卒于家”,即生于公元104年。按平均每代间隔28年±4年的传代规律推算,寔父“翔”应生于公元75年前后。按这个时间计算,翔在第一次受党锢之祸,已有90岁的高龄了。试想,一个90岁的老人还能从事党事活动而被株连吗?如果他们真是父子关系,而又同时受党锢之祸入狱,岂不是天大的奇闻?像这样带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史书岂有不载?这就说明他俩不是父与子的关系。
再以同时坐党事件中一些人的生年作比较,翔不应生于公元75年前后。如:司棣校尉李膺(110—169),与李膺齐名的杜密(?—169),光禄勋主事范滂(137—169),太学生首领郭泰(128—169),文学家、书法家蔡邕(133—192),司徒王允(137—192),荆州刺史刘表(142—208),司空荀爽(128—190),太常赵岐(108—201),太丘长陈寔(104—187)等。从以上坐党事件十人中,竟无一人生于公元75年前后,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太丘长陈寔,生于公元104年。党锢之祸时,陈寔已60余岁,早已成为宗师级名士,像荀爽、贾彪、李膺、韩融、王烈、管宁、华歆、邴原等都曾向他问过学。在涉及党锢之祸的人群中,株连陈寔之徒200余人,作为老师陈寔,年龄较大是情理之中。无怪乎他竟发出“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之大义凛然的壮语,因为他是老师,理应为人师表。所以其他坐党事人的生年,一般不会大于公元104年。据此推断,陈翔的生年至多是在公元104年左右,很可能在公元104年以后,而绝不会生于公元75年前后。因此,时间就能证明翔与寔不是父子关系,也不可能成为父子。
三是从翔与寔生长不同地方,间接证实翔与寔的父子关系是不存在的。
《后汉书·陈翔传》载:“陈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汝南邵陵,即今召陵,在河南省平舆县北。而部分颍川陈氏族谱又载:翔,字子麟,山阳瑕丘人。山阳瑕丘,即今山东省兖州县东北。同一个御史中丞陈翔,《后汉书》与部分颍川陈氏族谱所载的生长地却不同,此疑一也。《后汉书·陈寔传》载“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即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古桥乡陈故村。颍川许昌与汝召陵相距100多公里,与山阳瑕丘(谱云翔之生长地)相距数百公里。既然翔与寔是父子关系,他们的生长地竟相差如此之远,此疑二也。同时,不管汝南召陵陈翔迁颍川生陈寔也好,还是山阳瑕丘陈翔迁颍川生陈寔也罢,都不符合《后汉书》关于陈寔“出身卑微”和家境贫寒的记载。若依据《后汉书》,就不存在山阳瑕丘也有一个陈翔。这是族谱强行附上去的。
四是根据《后汉书·陈翔传》关于翔“坐党事……卒于家”的记载证明,这里的“家”当指汝南召陵,而不是许昌。因此,陈翔没有迁居许昌长葛生陈寔,为明摆着的事实。
五是根据《后汉书·陈翔传》载翔“祖父珍”,而《唐表》载陈寔曾祖父是“齐”,这就证明翔与寔不是父子关系。可是也有宗谱说陈寔曾祖父为“珍”,那也是在套用《陈翔传》而来的。
总而言之,陈翔与陈寔不是父子关系,成为定论。因此,关于陈寔的上下几代传承世次,在没有新的资料出现之前,当依《唐表》。